我那个补习班的等候区,像一个被时光按下慢放键的角落。
每天下午五点半过后,这里便会渐渐挤满人,消毒水的淡味顺着空调风漫过来,混着不同家长身上的气息——年轻妈妈身上清甜的护手霜味,中年父亲指尖残留的烟草味,刚从菜市场赶来的外婆衣角沾着的青菜露水味,还有写字楼职员西装上未散的咖啡因气息。
这些味道缠绕在一起,酿成一种独属于等候的、略带焦灼又暗藏温柔的气息。
日光灯管悬挂在天花板上,用了有些年头,发光时带着轻微的嗡嗡声,光线算不上明亮,却足够把一张张脸照得清晰。
我总爱站在前台的角落,假装整理教具,实则悄悄观察这里的一切。
穿格子衬衫的男人对着手机屏幕皱着眉,手指飞快地回复工作消息,时不时抬头看一眼教室门口的时钟;扎马尾的女人正低头给孩子织围巾,银针在指尖翻飞,毛线球滚到脚边,她弯腰去捡时,眼角的细纹在灯光下闪了闪;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戴着老花镜,手里捧着一本翻得卷边的育儿书,时不时推推眼镜,眼神里满是认真。
他们大多沉默,偶尔交谈,话题也总绕着孩子——“这次数学又考砸了作文还是写不出来报了这么多班,不知道有没有用”。
可就在这些细碎的话语间隙,在一杯温水递出的瞬间,在一声被刻意压低的叹息里,那些被生活磨得平淡无奇的故事,就像藏在旧衣口袋里的糖纸,轻轻一掏,便露出了里面褶皱的、带着点苦涩的微光。
我记得那个开出租车的张师傅,每天接孩子前都会提前半小时到,坐在最里面的座位上,拿出一个用了多年的搪瓷缸,泡上一杯浓茶。
有一次我问他怎么来得这么早,他笑了笑,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:“跑车累,这里安安静静的,能歇口气。”
后来才知道,他妻子常年卧病在床,家里的重担全压在他身上,每天只有这半小时,能暂时放下方向盘上的疲惫,不用想油费、不用想医药费、不用想明天的生计,只是安安静静地等孩子下课。
他说:“看着孩子跑出来的样子,就觉得日子还能撑下去。”
还有那个做保洁的李阿姨,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,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布包。
有一次孩子上课迟到,她急得眼圈发红,跟我道歉时声音都在抖。
后来聊天才知道,她每天要打三份工,早上五点就去小区打扫卫生,中午去餐馆洗碗,下午赶过来接孩子,再送孩子去晚托班,自己又去夜市摆摊。
她说:“苦点累点没关系,就想让孩子能好好读书,别像我一样,一辈子只能干力气活。”
她说话时,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布包,里面是孩子昨天考了满分的语文卷子,被她叠得整整齐齐,像件稀世珍宝。
他们是写字楼里加班到深夜的职员,是菜市场里为几毛钱讨价还价的摊主,是骑着电动车穿梭在风雨里的外卖员,是把所有温柔都给了孩子、却把疲惫藏在眼底的父母。
他们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,没有波澜壮阔的转折,只有最平凡的挣扎——为了柴米油盐的奔波,为了孩子前途的焦虑,为了那些说不出口的遗憾的沉默。
他们的喜怒哀乐,像水滴融入大海,悄无声息,无人在意。
很多时候,我会想起自己刚成为教培老师的日子,总觉得这份工作平淡无奇,首到我开始认真倾听这些故事。
我发现,每个看似普通的人,心里都藏着一片深邃的海,里面装着未曾实现的梦想、无法弥补的遗憾、和那些连自己都快遗忘的温柔。
这些故事,像落在窗台上的灰尘,被阳光一照,才显出细密的纹路;像飘在风里的柳絮,看似轻盈,却带着对土地的眷恋;像深夜里未接的电话,响过之后便归于寂静,却在心底留下淡淡的回响。
我开始把这些故事一一记下,在深夜批改完作业后,在周末安静的办公室里,用一支普通的钢笔,写在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。
我不是什么作家,也写不出华丽的辞藻,只是想把这些无人倾听的心声,这些被时光忽略的角落,好好地存放起来。
于是,便有了这本《无人在意的故事》。
它没有惊心动魄的传奇,只有最真实的人间烟火;没有深刻的人生哲理,只有最朴素的喜怒哀乐。
我把它献给每一个在平凡生活里默默前行的人,献给那些被忽略的、却依然闪闪发光的平凡人生。
因为我始终相信,即使是最微小的故事,也值得被倾听,即使是最平凡的生命,也自有其重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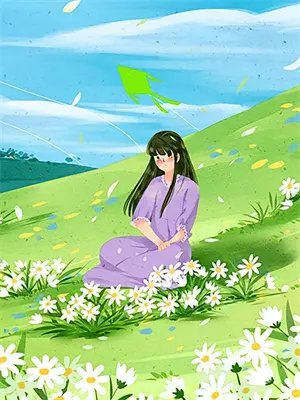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